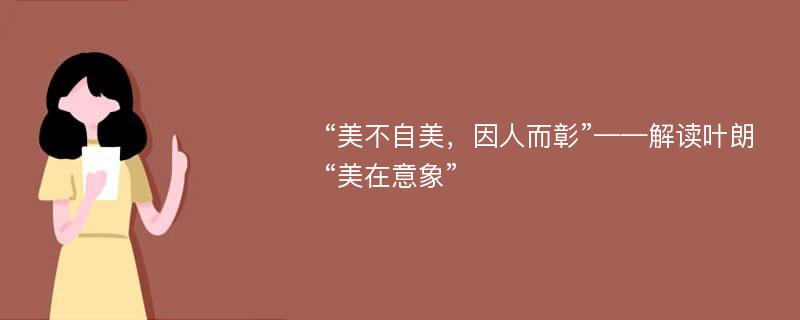
李月西藏民族学院
【摘要】“美”是一个复杂的概念。纵观中西方美学史,对“美是什么”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。叶朗将“美”归结为审美意象,这为中国现代美学体系做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。本文以柳宗元“美不自美,因人而彰”为命题作为理论切入点,具体分析叶朗运用意象本体论对“美”的阐释,及对当代美学研究中存在的理论弊端问题的解决。
【关键词】叶朗意象“美不自美,因人而彰”
【中图分类号】I207.62【文献标识码】A【文章编号】1674-4810(2011)01-0029-03
叶朗的“意象”论美学是长期研究中西方的哲学、艺术、美学等方面的理论结晶。他以广博的胸襟吞吐中西文化,把握了最具中国民族本土特色的美学精神的理论形态。叶朗以“意象”作为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对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中的片面化、机械化倾向的摆脱与克服。
一“意象”的概念
“意象”这个概念成为一个词之前,“意”与“象”分别使用在《山海经》中。将“意”与“象”放在一个句子中,最早出现于《周易系辞》。“意象”作为一个词最早可追溯到王充的《论衡》里,而正式把“意象”引入到文学理论中,则始于南朝的刘勰。
刘勰之后,将意象理论作为理论范畴加以考察,可以说是在唐代确立起来的。在宋元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,而在明清两代基本趋于成熟,清代的王夫之则提出“诗无达志”,表明诗歌审美意象的多义性特征。
在中国当代美学界,叶朗通过对中西方现当代美学的研究和反思,对“意象”的美学内涵做了最具有中国民族本土特色的理论阐释。一方面,他反对西方的“主客二分”思维模式;另一方面,在继承中国传统美学的基础上,对朱光潜、宗白华先生关于“意象”理论又予以批判的继承。首先他认为,朱光潜在《诗论》中所用的“意象”实际上应理解为“表象”,而“诗的境界”才应表述为“意象”。其次,叶朗明确指出,宗白华先生使用的“灵境”就是“意象”,而非“意境”;并认为“意境”与“意象”不是同一个概念。“意境”是“意象”,但并不是任何“意象”都是“意境”。“意境”除了有“意象”的一般规定性之外,还有自己特殊的规定性。因此,他郑重提出,应该“从朱光潜‘接着讲’”,要回到中国哲学和美学所具有的那种注重“天人合一”、重体验、“美不自美,因人而彰”的“意象”论传统,并在《胸中之竹》中第一次提出了“美在意象”。
二“意象”形成的前提
意象,简而言之,就是“意”与“象”的有机结合。什么样的“景”才能让人寄之以“情”?当人们欣赏同一处“景”时,为什么引发的“情”又千差万别呢?这就需要在纵深层次上解析“意象”形成的前提。
1.具有审美性质的“象”
为什么我们欣赏自然美会选择花朵、月亮,欣赏社会美会选择飞机、摩天大楼,欣赏人体美会选择身材高挑的美女呢?这是因为这些事物本身具有着客观的审美性质。李斯托维尔曾说:“审美的对立面和反面,也就是广义的美的对立面和反面,不是丑,而是审美上的冷淡,那种太单调、太平常、太陈腐或者令人太厌恶的东西,它们不能在我们的身上唤醒沉睡的艺术同情和形式欣赏的能力。”他认为,主体的“情”和“景”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交融、契合沟通的。那些平凡的、陈腐的、令人厌恶的“象”,根本不可能激起主体的美感,因而主体不可能进入审美活动,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“意象”。也就是说,审美主体选择的“象”不仅不是遏止消解美感的产生,而是会促使美感的发生,那么这就使得“象”要具有审美的性质。
2.存在于社会文化环境语境下的主体之“意”
同样是花卉,但对于高考落榜的学生来说,再鲜艳的花朵也无法进入他们的审美视野。同是一部《红楼梦》,看法却各有不同。不仅同一对象,不同的审美主体的审美存在个别差异,而且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下也会存在审美差异。杜甫“我昔游锦城,结庐锦水边。有竹一顷馀,乔木上参天”,而以后对竹子的描写又有“新松恨不高千尺,恶竹应须斩万竿”,这些都说明了个人的审美经验的内容并不是固定不变的,而是具体的、历史的,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。
“审美心理结构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历史的产物,它所构成的审美经验是来自社会文化的,由这种审美经验提炼而成的审美观念、审美趣味、审美理想更直接地与一定的社会生活、一定的社会价值意识相联系,因而渗透着这种审美价值意识的审美心理经验,必然随着社会生活、文化心理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,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、民族、阶级的情调和色彩。”因此,在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,当具有审美性质的“象”符合主体之“意”,且主体对之进行审美观照并达到了景中含情、情中见景的完整的、充满意蕴的感性世界时,便形成了“意象”。
在中国美学界,曾有这样一种观点,认为“美”是客观的。例如,黄山的迎客松是种客观存在,那么它的美也是一种客观存在。这是错误的。它否定了在历史环境下生成的审美情感的丰富性和差异性。不同时代、阶级、民族的人们对美的看法是千差万别的,这就使得人们无从考证“美”。而叶朗提出的“美在意象”则解决了这一问题。
三“美不自美,因人而彰”
唐代思想家柳宗元在《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》中有这样一段表述:“夫美不自美,因人而彰。兰亭也,不遭右军,则清湍修竹,芜没于空山矣。”在这里柳宗元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:只有在审美活动中,通过审美主体的意识去发现“景”(清湍修竹),并“唤醒”它,“照亮”它,使这种自然之“景”由实在物变成一个完整的、有意蕴的、抽象的感性世界即“意象”时,自然之“景”才能够成为审美主体的审美对象,才能成为美。也就是说,“清湍修竹”作为自然的“景”是不依赖于审美主体而客观存在的,美并不在于外物自身,外物并不是因为其自身的审美性质就是美的(“美不自美”),美离不开人的审美体验,只有经过人的审美体验,自然景物才可能被彰显出来,“彰”就是彰显、发现、唤醒、照亮(“因人而彰”)。
无论在东方,还是在西方,表述过类似的说法有很多。孔子的“知者乐水,仁者乐山”,庄子的“山林与!皋壤与!使我欣欣然而乐与!”,萨特也曾说:“这颗灭寂了几千年的星,这一弯新月和这条阴沉的河流得以在一个统一的风景中显示出来,这个风景,如果我们弃之不顾,它就失去了见证者,停滞在永恒的默默无闻的状态之中。”这些表述都是说,美依赖于人的意识,有待于人去发现,去照亮,有待于人的“意”与自然的“象”的沟通契合。
关于柳宗元的“美不自美,因人而彰”这个命题,叶朗将其分为三个层面来理解:
1.美不是天生自在的,美离不开观赏者,而任何观赏者都带有创造性
叶朗认为,美离不开人的审美活动,美在意象。这个意象世界不是一种物理实在,也不是抽象的理念世界,而是一个完整的充满意蕴的感性世界。用宗白华先生的话就是“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,成就一个鸢飞鱼跃、活泼玲珑、渊然而深的灵境。”不难看出,叶朗将自然界存在的物理之“象”(物)与情景交融形成在主体头脑中的抽象的“意象”之“象”做了严格的区别。“‘象’是‘物’向人的知觉的显现,也是人对‘物’的形式和意蕴的揭示。当人把自己的生命存在灌注到实在中去时,实在就有可能升华为非实在的形式——象”。
太阳,作为物质实体的“象”,虽然具有审美性质,但未必能进入审美活动中。太阳在做农活的庄稼汉眼里,是“毒辣辣”的,不是美的。就是说,作为物质实体的“象”,它只有激发起欣赏者的美感,并使主观情感与之交融形成了“审美意象”时,才是美的。不同的观赏者会形成不同的“审美意象”,因此“意象”包含着人的创造性。即使某一物具有审美性质,若无人欣赏,也不能成为美。美离不开观赏者,任何观赏者都带有创造性。这就是叶朗运用意象论对“美不自美,因人而彰”的第一层含义的理解。
2.美并不是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
叶朗认为,美是客观的,美没有变化,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观点是错误的。这说明不同的观赏者由于个体审美理想、审美趣味的差异,即使面对同一“象”时,也会产生不同的“审美意象”。
同样是秋天的枫叶,在不同人的眼里,则有着不一样的情怀。杜牧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不难想象,杜牧以一种悠然闲适的心情欣赏这随风飘洒的枫叶时,心中的枫叶早已变了模样,比那二月的鲜花还要红艳呢!此时的枫叶在杜牧眼里,是一个充满着收获与欢乐的意象世界。而在西厢记中则有“晓来谁染霜林醉,总是离人泪。”秋天来了,万物凋落,莺莺因爱而感伤,在她的眼里,秋天的枫叶像是被泪水染过一般,是一个充满伤感心碎的意象世界。而在戚继光那里则是“繁霜尽是心头血,洒向千峰秋叶丹。”这又是另一种意象世界。在国家存亡的危难之际,他抛开个人情愫,充满着忧国的情思,这里的枫叶又呈现出一种豪迈悲壮的感情色彩。
同是枫叶,但是不同的人们形成的意象世界不同,给人的美也就不同。这就是叶朗对“美不自美,因人而彰”的第二层含义的理解。
3.美带有历史性
叶朗认为,应站在社会历史性的高度,将个体的差异性放到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角度来加以考察,运用意象论阐释“美”。
(1)审美的时代差异。个体的审美意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,处于某个时代的个体其审美经验都免不了被烙上时代的印记。《诗经》中的名篇《关雎》长期以来被人们解释为咏后妃之德,而今天的人们早已把它看做一首爱情诗了。不仅如此,从服饰上也可感受到时代的变迁。满清时期,男子要求留长辫,着马蹄袖,女子着旗袍;民国时期,代之以中山装;而五四运动前后,男子则长衫西裤加围巾,女子则短褂长裙,这是反帝反封建、追求科学民主时代精神的体现。新中国成立后,全国的衣料的主色调单调沉闷,以深色为主。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环境氛围的宽松,服装的各种款式便丰富起来。可见,服饰也是时代的一面镜子。
(2)审美的民族差异。由于不同的民族在生活习惯、思想文化传统、心理及感情等方面的不同,这使得他们的审美感受存在着巨大的差异。在日常生活中,有的民族把肥胖看成蠢和丑,而埃及人却认为丰润肥胖是美的。有的民族以“齿白唇红”为美,而马来半岛有的民族认为白齿是犬牙,将其看做是丑。在京剧脸谱中,白脸暗示阴险狡诈,黑色则象征刚直不阿。可见,由于不同民族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,使得他们做出了不同的审美判断。正如黑格尔所说:“如果我们看看欧洲以外各民族的艺术作品,例如他们的神像,这些都是作为崇高的值得崇拜的东西由他们想象出来的,而对于我们却会是最凶恶的偶像。他们的音乐在我们听来会是最可怕的噪音,反之,我们的雕刻、图画和音乐在他们看来也会是无意义的或是丑陋的。”
(3)审美的阶级差异。所谓的阶级,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而产生的,是与社会功利直接联系着的。不同的阶级体现出的阶级、阶层的意识、愿望是恰恰相反的。体现为审美也是如此。《水浒传》向我们带来的情感是“造反有理”,反应了广大农民的审美愿望和理想。而在《荡寇志》中却把农民的形象刻画得如此丑陋,成为“贼寇”。在中国历史上,也不乏这样的例子,“楚王好细腰,宫中多饿死”,楚灵王喜好细腰,无论男女凡是腰围粗大就厌恶,于是从宫中到朝廷都软带紧束,后来就遍及全国。这种好腰之风之所以能够蔓延开来,是与权贵们鄙视劳动,沉溺于奢华的生活,迎合权贵分不开的。这个例子明确地告诉我们,审美是带有阶级性的。
即使具有相同审美性质的审美对象,由于主体受阶级、民族、时代的文化环境的影响,也会产生美感差异。这就是“美不自美,因人而彰”的第三层含义。
可见,在审美过程中,主体的“意”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,某个具体的个体(他)只能选择能够使自己产生美感的,符合他自己的审美经验的“象”来作为情感的寄托,从而达到寄情于景、情景交融的一气流通的“审美意象”之美的境界。而此时形成的“意象”不同于客观存在的物理之“象”,已是人们头脑中的“美之象”,它是具体的,是以个体存在的,是专属于他自己的美。
美是客观的观点,最根本问题在于否定了美是社会性历史性的文化活动。而叶朗的“美在意象”不仅肯定了在审美活动中事物的审美性质的重要性,而且也更加强调了审美情感的关键性,将主体的审美情感放到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环境下加以考察,以此来说明美是历史的范畴,是社会性、历史性的产物,没有永恒的美。
但是笔者认为,叶朗从意象论出发来阐释美的本体,也存在着理论弊端。首先,叶朗将审美活动看成是一种意象性的活动。这是不合适的。审美对象是由审美客体通过审美观照生成的,不是人主观头脑中的审美意象,不是意向作用下的结果。如果审美活动是意向活动,审美对象必定是一种意象,而每个人头脑中的想象都是不一样的,从而审美对象也就无法认识了。其次,审美客体与审美对象概念上的混淆。当花朵引起了主体的愉悦与满足时,它是审美对象,但不能因此就说花朵是审美对象,因为当它离开了主体的审美观照便只是审美客体。审美客体是审美的可能性,而审美对象是审美的现实性。马克思曾说:“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的成为衣服,一栋房屋无人居住,事实上就不能成为现实的房屋,一条铁路在通车之前,只是一条可能的铁路,只有通车之后才是一条现实的铁路。”
叶朗以“意象”为核心建构起了意象本体论美学体系,虽然存在着理论的弊端,但在中国当代的研究领域具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,对于“意象美学”我们要予以批判的继承。
参考文献
[1]李斯托维尔.近代美学史评述[M].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1982:232
[2]杨恩寰.美学引论[M].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05:221
[3]蒋沛昌.论语今释[M].湖南:岳麓书社出版,1999:127
[4]庄子知北游[M].上海:古籍出版社,2007:226
[5]叶朗.美学原理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9:34、44
[6]宗白华.美学与意境[M].北京:人民出版社,1987:210
[7]黑格尔.美学(第一卷)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81:55
[8]马克思、恩格斯.马克思恩格斯全集(第四十二卷)[M].北京:人民出版社,1972:125
